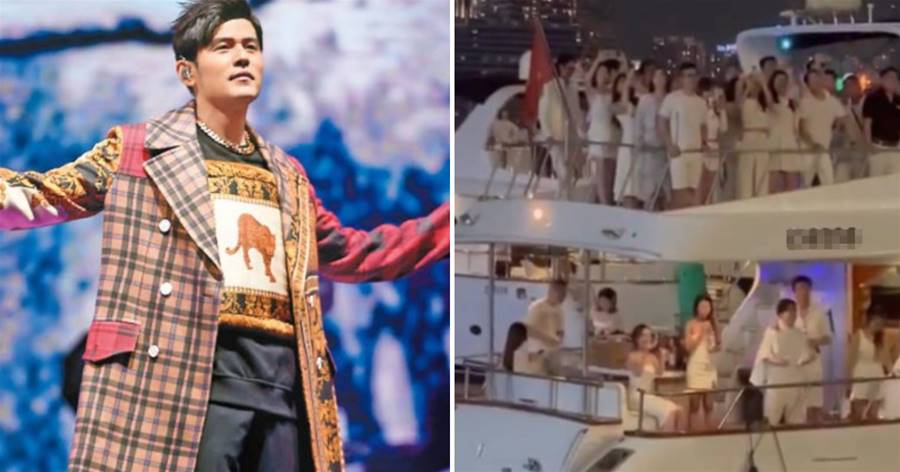文 |老涵
編輯 |老涵
匈奴族的民族起源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術界激烈爭論的話題。早在19世紀,人們就試圖將他們與希臘文獻中出現的民族聯系起來,如弗里諾伊和普哈諾伊,這導致了死胡同。
在語言學證據的基礎上,人們已經作出了勇敢的努力,至少要確定匈奴的語言歸屬。匈奴與由匈奴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組成的「韃靼人」種族的認同,可以追溯到18世紀法國文學家德格涅斯。
這個理論是受匈奴是入侵羅馬帝國的匈奴人的祖先的啟發,一直流傳到20世紀。赫斯、德格魯特和希拉托里都支持「土耳其」等式。
中國資料的民族「Ti」被認為是早期轉錄土耳其人的名字,這當然給這個流行的論點增加了貨幣。
匈奴的祖先也被認為是其他民族,比如賢云;事實上,根據普里薩克的說法,孫宇、賢云、秦榮和其他一些人都來自一個共同的民族宇宙,匈奴也屬于這個民族宇宙。
卡爾格倫在語言證據的基礎上駁斥了匈奴與賢云的認定。哈隆和馬斯佩羅否認中國北方的部落,如提人和榮格人,是「土耳其人」,事實上,他們認為后者更接近中國人,而不是阿爾泰人,這一論點後來得到了克里爾的支持。
利蓋蒂是第一個質疑匈奴語的阿爾泰語假說的正確性的人,他開始走另一條路線,使他進入南亞的亞尼塞語,特別是奧斯提亞克語。
普萊布蘭克進一步提出,他在1962年得出結論,匈奴說的是葉尼塞族的一種語言。因此,似乎出現在匈奴語言中的阿爾泰元素被解釋為最初是西伯利亞語,但後來被突厥人和蒙古人借用,他們來建立自己的語言大草原上的各州。
另一方面,貝利認為匈奴是說伊朗語的,而杜爾弗否認了匈奴語與任何其他已知語言之間的關系,并以最強烈的措辭拒絕與土耳其語或蒙古語有任何聯系。
就目前而言,我們不能超越這樣的結論:即小奴聯盟是不同民族和語言群體的混合體,盡管它的「國王」語言——在中國記錄中所代表的程度——目前還無法識別。
遵循傳統建立的施氣和後來中國歷史,大多數學者在中國接受工作的假設認為匈奴的后代出現在早期的來源——鄭,蒂,賢,等等,與此同時,後來的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祖先。
在一項有影響力的研究中,王國偉證實了商周時期的貴芳、坤、玄、賢云、春秋時期的榮提、戰國時期的胡都屬于和匈奴人是同一個民族。
梁志忠和其他幾位30年代的歷史學家也持這一觀點,但并沒有被普遍接受。
其他人則認為匈奴人的祖先與中國人沒有什麼不同,而且是在公元前六世紀。他們建立了一個賢云國家:中山。
根據這一解釋,這發生在公元前295年。當中山被趙摧毀后,其人民遷移到內蒙古和寧夏的中部領土,匈奴領袖摩頓後來成為他們的契安宇,并形成了匈奴聯盟。
匈奴與中國人有親緣關系的理論來源于柴志書中的一段文字,據說匈奴是夏配偶氏族的后裔。
然而,一些學者拒絕了這一論文。在195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孟文東堅持認為桂芳、廣義、洪密和賢云不是真正的賢奴,而是與熊奴的祖先有血緣關系。
黃文皮還認為,昆芳、洪米和賢云與秦家族有關——通常被歸類為原始藏族,而不是匈奴民族,林胡和樓凡是唯一產生匈奴國家并構成了其核心的群體。
另一群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學者傾向于認為匈奴不是遠東民族,而是來自西方。
林陸志按照類似的思路,試圖建立一個民族系譜樹,可以解釋資料中出現的所有外國人;他關于外國人與中國關系的歷史分六個階段發展,并在創造中達到頂峰匈奴州的成員。
他在1962年的著作中假設了北方提和匈奴之間的聯系。
在他的《匈奴全史》中,林直并沒有試圖在匈奴和他們假設的前輩之間建立民族和歷史聯系,而是在一個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框架內解釋了匈奴聯盟的形成過程。
根據林的說法,戰國時期,某些榮氏和提部落聯合起來,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這些人隨后「進入文明」,建立了匈奴國家,而那些一直落后的人(如東虎)仍處于部落階段。
匈奴州最終是一個基本自治的結果鄭和提部落的發展定居在戈壁沙漠的北部和南部,後來由從中山邦的逃亡者加入。
其他曾在黃河平原定居的榮格和提,後來被中國國家吸收。因此,匈奴被認為是一個混合的群體,包括了所有以前活躍在戈壁北部和南部的民族(呼宇、貴芳、賢云、鄭、帝和胡)。
至于匈奴最初是否形成了一個單一的部落,林菅根據語音相似性,傾向于與匈宇、久芳、賢云更接近。
在討論匈奴的民族身份時,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一樣,也討論了突厥、蒙古、芬蘭-烏格里亞或印歐從屬關系的相對合理性。
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是蒙古血統的,但這一點仍然存在爭議。蒙古學者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匈奴是原始蒙古人,從歷史上蒙古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他們。
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官方史學堅持認為,「關于社會發展、習俗和文化,匈奴人[即。」,匈奴]與通格斯族的原始蒙古部落非常接近。
筆者認為:匈奴人很有可能是蒙古人,但後來,在他們占領了「西部領土」(東突厥斯坦,中亞)后,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被突厥部落同化了。"
鑒于長期的語言學和語言學辯論仍然沒有定論,假設匈奴作為蒙古帝國建設者的種族祖先的簡單解決方案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了,近年來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和政治進程上。
因為匈奴統治著第一個歷史上記錄記載的亞洲內部帝國,人們問這個帝國為什麼以及如何產生,以及它是真正的一個帝國,還是一個松散地在一起的部落聯盟。
游牧社會的自治演變有時被認為是要達到與「早期國家」相當的復雜性水平和大規模動員能力的原因。
埃伯哈德提出了一個相當古怪的假設,他設想了三種游牧社會模式——西藏、蒙古和土耳其——每一種都由特定類型的牧區專業化定義。
其中最先進的是「土耳其」型,是一個分為部落和專門飼養馬的社會——與蒙古和西藏模式的羊和牛的專業化形成對比——其特點是形成一個社會以及部落的政治等級制度。
這些養馬的部落的遷移范圍比其他模式更廣,這使他們與其他部落有了接觸。
因此,這些游牧民族發展了經驗豐富的軍事和外交領導,這反過來又負責國家的建立。事實上,這些獨立的專業化模式,加上種族和語言上的聯系,不能在歷史分析的層面上進行檢驗。
克拉德廣泛研究了牧區游牧民的社會結構以及國家形成的問題,并假設存在兩個相互依賴的專業社會,農業和牧區,以及兩者之間的整個大陸的交換網絡。
在這一方案下,游牧民族階級分化的發展與牧民剩余部分對農產品的交換有關。由于貴族控制著交換,并向平民索取貢品,國家的演變源于這兩個對立階級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
根據克拉德的說法,戰爭、掠奪和征服是由于交換機制的缺陷而造成的貿易中斷而造成的異常情況。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中心是在游牧社會產生盈余的內部能力之內。
筆者認為:基于傳統的社會階級和社會的貿易,當我們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國家形成的具體實例上時,這一計劃的吸引力往往受到質疑。
例如,當莫登上台時,交換機制出了什麼問題?他在這個機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這個全大陸的交換網絡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交換的數量是多少?為什麼在某些時候,對貿易施加的限制不會產生任何軍事沖突,而在其他時候,邊境市場的開放之后,會立即出現大規模的突襲遠征隊呢?
我們真的能減少中亞地區的居民嗎他們進入了經常交戰的部落,一個大型的動物飼養者協會?最后,為什麼一些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仍然沒有國籍?
這些由歷史記錄本身產生的問題不能在克拉德的計劃中得到回答,特別是因為「游牧」社會和政治單位的經濟基礎通常包括各種類型的生產,其中畜牧生產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
人類學研究表明,田園游牧社會很少能夠脫離其他經濟,特別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而繁榮起來;
此外,歷史上的資料中充斥著關于游牧民族掠奪定居民族的報道。基于這些前提,這種「依賴」理論假設,國家形成的現象與游牧民族對其經濟中缺乏的基本必需品的長期需求有關。
由于田園經濟的「非自治制」,游牧民被迫與農民進行貿易或襲擊他們。然而,突襲是小規模的企業,直到定居的國家使邊境更加安全,實施了新秩序。
為了向這些國家施壓,迫使它們屈服于他們的經濟需求,游牧民族將創建自己的規模更大的政治實體,由「超部落」政治階層管理,主要負責軍事遠征,并管理來自軍事國家的「勒索」。
根據根據這一理論,「超部落」游牧組織將成為對一個強大的定居國家的回應,在這個國家下,小部落無力,因此「迫使」游牧民族組織成更大的政治聯盟。
游牧民族依賴于中國農產品的假設前提了許多條件,即游牧社會單位的生產排除了自給農業,游牧民族和中國之間存在著谷物的交換制度可以獲得牧區,中國有剩余的農產品可以與游牧民族進行貿易,最后,除了中國,游牧民族沒有其他谷物來源。
《野蠻人通過中國人的眼睛:研究種族差異的人類學方法的出現》
《華盛頓:人類研究所》
《三代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中國文明起源的過程方面》
《中國古代考古學》
《中國文明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