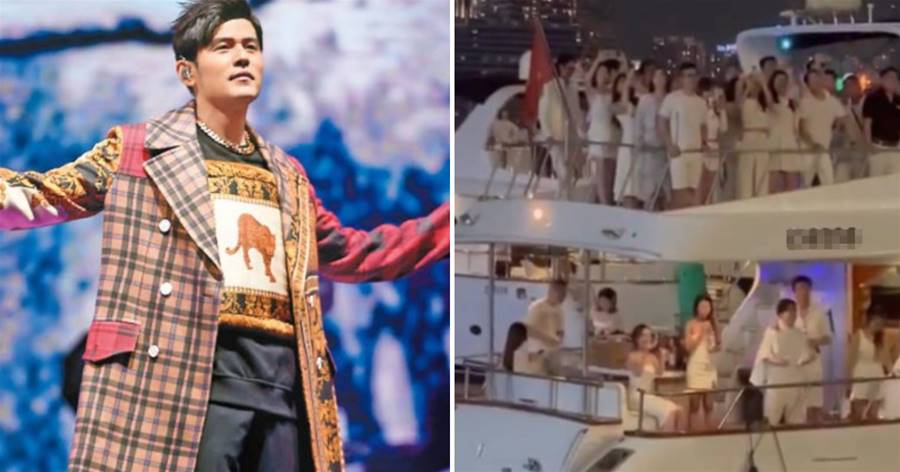即便是寫給父親的歌,MV里往往也只有一個人的身影。
父親是男人最難完成的角色,它既關乎規則又考驗人性。樂壇中有許多值得一提的寫父親的歌,歌曲里有感懷,有眷戀,有直白控訴,也有無奈追思。
有些歌詞流出來只需半小時,有些歌詞寫完就是半輩子。
前者,比如父親寫給兒子,那里面有對一個未知個體的期許;此刻的父愛是可以觸碰的實體,沉厚綿長,如暖暖涓流環繞著襁褓。
后者,比如兒子寫給父親,那個未知的個體猛然長成了獨一無二的成人模樣,懂得了感恩,更明白了如何獨立思考、反叛與抗爭;此刻的父愛時常變得窘迫,父子之間常被心煩的亂流裹挾——兒子急于從原有的語境中突圍脫困,而父親急于想知道為何兩人無法再溝通。
他們都找不到答案,即便知道答案也開不了口,開了口,也很難好好說話。

父親是男人最難完成的角色,幾乎沒有之一。它既關乎規則又考驗人性,如果偏向某一邊,注定做不好;即便平衡了,也未必會得到想象中的肯定。
傳統的父子關系出名僵硬。大多數父子之間,不可能存在「妳若決定要做最尾一名絕對允許」「早習慣看開/妳易容還是可愛/最重要心記得要開/來競技角力賽/最終不管輸贏都一般可愛」的極致寬容。這幾句歌詞,來自陳奕迅的《大個女》,林夕填的詞——女兒可以被寬容寵溺,甚至被允許「不思進取」,沒關系,老爸寵著妳,沒人能欺負妳。
可是抱歉,兒子不行。
李宗盛創作半生,佳作無數。他寫遍愛情得失、友情勵志、凡俗人間、少年夢想和中年危機,精于深刻入骨的反思,其誠懇讓很多人不忍細聽,聽來全是心底最深的難過。他曾11次入圍台灣金曲獎最佳作詞候選(與方文山并列第一),憑《給自己的歌》(2011)、《山丘》(2014)兩首自傳體歌詞拿過兩次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
而李宗盛在2019年第三次奪此殊榮,是2018年寫給亡父的《新寫的舊歌》。

《給自己的歌》《山丘》用的都是李氏獨有的念白唱腔,一字一頓地反思人生、感嘆時光:「等妳發現時間是賊了/它早已偷光妳的選擇」「越過山丘/才發現無人等候」,滿是追悔自嘲,主題大都是男女之情——可選擇的對象幾乎沒了,等候的人也早不在了,伴著「想得卻不可得/妳奈人生何」的寂寥。除此之外,李宗盛還唱過「寂寞難耐」「最近比較煩」「我從來不想獨身/卻有預感晚婚」,人到中年,各種不平。
只是,錯過的感情還能再找;逝去的,就徹底沒了。

《新寫的舊歌》早該寫了,但直到父親亡故李宗盛才終于成篇。它是一個老去的兒子對亡父的傾訴;它是不可逆的現實,是終于清醒的痛苦追思;它是最后的獨白,只能認認真真唱一次。不會有太多人在KTV唱它,因為沒什麼人喜歡在普通朋友面前被直戳心底,流露真情。
它不太像一首完整創作下來的「歌」,全曲有明顯的割裂感:主歌本來就很長,主副歌之間的過渡更長得可怕,轉接也遠不如《給自己的歌》《山丘》圓滑,但歌詞卻是完整而氣韻流暢的。
妳可以這麼看:《新寫的舊歌》是一段完整的話,只是恰好依字行腔,便有了曲。《新寫的舊歌》嚴格來說不是一首歌,而是李宗盛在父親去世后攪著半生念想,按著自己的手寫了篇文章,和著幾段曲給念出來了。它很難唱得圓順,畢竟這是一個「敷衍了半生的、沉甸甸的、將我拽回過去的命題」。
非一般的體裁與格式,與反思父子關系的過程一樣艱難曲折。

在李宗盛眼里,父親是什麼?
父親代表著殘酷又真實的生活。
在早期歌曲《阿宗三件事》中,李宗盛少有地提到了父親:一個讓自己扛著瓦斯罐行走于臭水四溢的夜市中、在電線桿上綁電話牌子的瓦斯行老闆。
沒有其他描述,父親的形象如此模糊,除了「謀生不易」四個字,看不出別的;自小成績很差的李宗盛,也只能接受大學聯考落榜、讀工專、扛瓦斯罐、一邊苦熬一邊努力還得不到認可,「有一卡車的難題」的真實人生。
人在成長過程中要面對許多困局:成長碰壁、感情吃癟、對原生家庭的糾結和反叛、對真實人生的接納和反擊。而父親,恰巧就站在那個殘酷現實的開端,面目冷漠又模糊。
父親像是生命里的旁觀者。
在李宗盛從「小李」到「華語音樂教父」的成長中,父親的作用極其微弱,似乎真的是一個徹底的旁觀者。《新寫的舊歌》里,李宗盛在「旁觀者」之前用了兩個定語——「若無其事」「刻意拘謹」,再用母親「憂心忡忡」的姿態作對比,襯出一個傳統的、僵硬的、無力的平凡父親形象。
父親無能也無力參與李宗盛的人生,給予嘉獎時也顯得吝嗇。父子倆都在忙碌生活中「卑微地喘息」,最后父親先停止呼吸,一切糾結和痛苦戛然而止。

父與子很難成為知己,但又不甘心只是甲乙。
《新寫的舊歌》中有兩句歌詞讓聽眾感觸最深:「兩個看來容易卻難以入戲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鳴」「兩個男人極有可能/終其一生只是長得像而已」。「父慈子孝」之類的表述看似理所當然實則很難做到,現實更可能是兩個幾乎沒有重要關聯的獨立個體,也可能是不善表達的父親和倔強叛逆的兒子,終其一生都在互相較勁和消耗。
與黃偉文作詞、陳奕迅演唱的《單車》情形相仿,兒子總會懷念小時候和父親融洽相處的快樂時光,從而對長大后父子關系的疏離一邊不解,一邊怨恨:為什麼我們不能如過去一般親密?為什麼好好說話那麼困難?
李宗盛在《新寫的舊歌》里,也表達了父子之間「不能成為知己」的遺憾:他先是擔心自己沒出息,費盡心機想驚喜,等到自己終于活明白、想開口時,父親卻已走了。
父親走了。與妳角力的、制約妳的、對妳施壓甚至施暴的那一方,有話卻說不出,總顯得漠然的那一方,徹底不在了。父子之間最初和最后的和解,似乎都是單方面的:那年妳剛出生,父親抱著一張白紙般的妳,言辭和表情中飽含著所有真誠;當妳跪倒在父親靈柩前時,所有情緒只能匯成一句從未對他說過的話:「當徒勞人世糾葛/兌現成風霜皺褶/爸,我想妳了。」

華語樂壇還有許多值得一提的寫父親的歌——除了晚會上那些讓父子都尷尬的主旋律歌曲。
其中有對父親的控訴。周杰倫的《爸,我回來了》是非正常家庭下的產物。相較一般父子關系的冷漠僵硬,生于破碎家庭的周杰倫眼中的父親恍如惡魔,筆下滿是不解和控訴:「我叫妳爸/妳打我媽/這樣對嗎?」
這首歌直白且致郁,在遭受過父親酗酒、責罵甚至家暴的人的心中,《爸,我回來了》像剜開傷疤的刀,把一個年幼孩子憤怒卻無能為力、備受創傷和恐懼的情景不加修飾地展露出來,最后完結于一個絕望的念頭——「如果真的我有一雙翅膀,兩雙翅膀/隨時出發,偷偷出發/我一定帶我媽,走」。這不僅讓有類似遭遇者心有戚戚,也讓不曾遭受家庭暴力的人不寒而栗。盡管後來周杰倫與父親關系有所修復,但這份童年的影響絕難估量。

許飛原作、李健翻唱的《父親寫的散文詩》,用父親寫日記的口吻慢慢訴說——沒時間看電影,時間得花在修縫紉機踏板、借錢和哄妻女上面;不忍看女兒瘦了,更不忍看她出嫁;現在老得像一張舊報紙、一個影子,未來終會老成一堆舊紙錢,但終究要趁有生之年勤加反思,并盡量為兒女多留下點什麼。這是一個凡人一生的眷戀、痛悔和努力,讓做兒女的聽者理解父親的不易,了解那份在世事消磨中保持初心不改的秉性。
因為我們忘了父親本是常人,會犯錯、有情緒、想有自己空間、需要理解關懷——反過來也是一樣;我們也忘了「愛多偉大/似杯清水/給我所需」的前提是親子之間互相的真誠關心,而非身份的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