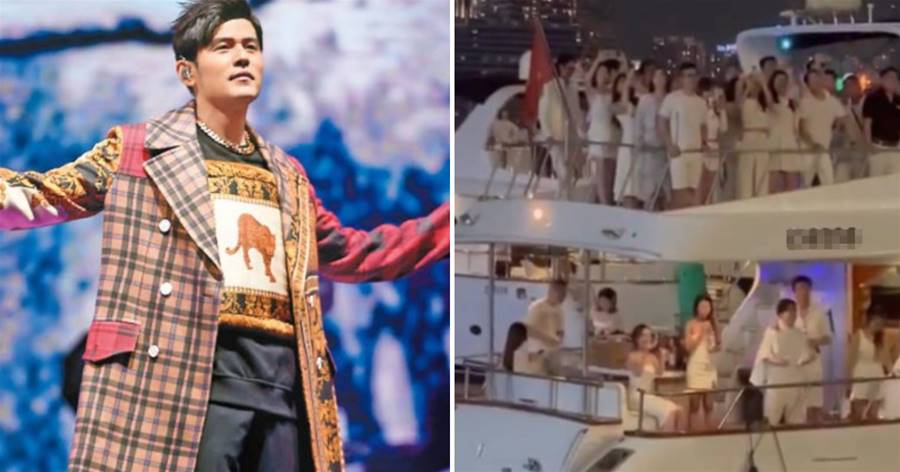隆美爾曾是希特勒手下的一員悍將,然而,無人料到,榮寵加身的隆美爾竟然在一個平靜的日子里被賜死,希特勒布下毒局,給了他別無選擇的選擇。
最終,隆美爾用十分鐘和家人們告別,勸阻了意圖反抗的妻兒,服下了毒藥,結束了軍人榮光的一生。
在隆美爾的兒子曼弗雷德的記憶里:「父親和母親對希特勒有一種宗教式的崇拜。」
這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希特勒對其統治下的納粹德國進行思想清洗,但客觀來說,希特勒對隆美爾的賞識和提拔又是一因。
1938年,希特勒在一個午后讀到了《步兵進攻》這本書,「進攻、進攻、再進攻」,他意味深長地念道。
合上大部頭,這是希特勒第一次正視「埃爾溫·隆美爾」這個名字,他決定接見他。
兩人相談甚歡,希特勒稱其為「了不起地軍事學家」,當即決定將儒雅沉穩地隆美爾提拔為元首大本營衛隊長、少將軍銜。
1940年5月,希特勒發動閃擊法國行動,隆美爾帶領第7裝甲師一馬當先,正是當之無愧的「先鋒官」。
在全場戰斗中,隆美爾身為將職,親自乘坐坦克,沖鋒在最前方,隆美爾這種幾乎將自己燒成灰燼的熱情與忠心令希特勒都為之震撼,暗中放心的同時,他也生出幾分擔憂,以至于不得不一遍遍地給隆美爾發送電報:「你幾乎讓我夜不能寐,所有人都在擔心你的安危。」
6月,作戰取得重大突破,在40天的戰斗中,隆美爾地裝甲師向前推進350多千米,此一役令隆美爾獲得了希特勒親自頒發的「騎士鐵十字勛章」。
然而,在榮寵之下,也暗伏著細密的危機。
1942年11月,隆美爾在北非戰場陷入危機之中,艾森豪威爾指揮的美軍在卡薩布蘭卡登陸,德意軍隊遭到了英美夾擊,1943年3月,希特勒將隆美爾召回了德國。
還未等有所行動,同年5月,隆美爾便在廣播中聽到了25萬德意士兵在突尼斯投降的消息,那是一個黑暗的黃昏,沉郁的廣播聲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此時,隆美爾憂心地望向希特勒所在的方向,他仿佛聽到了第三帝國的挽歌。
1943年時,隨著戰況的惡化,希特勒的身體也日漸衰弱,他開始喜怒無常,猜忌一切,朝令夕改。
1943年7月,足足賦閑4個月的隆美爾被希特勒任命為駐意大利北部的集團軍司令,所有人的都知道,所謂的「暫定」、「觀望」不僅僅針對戰爭,更是在希特勒在審視隆美爾。
根據當時的局勢,盡管此時他不再表達對隆美爾的擔憂,并對隆美爾的家人多加監視,但是守衛「大西洋壁壘」的行動仍缺不了這員猛將坐鎮。
1944年7月17日,在諾曼底登陸計劃開始后的第6周,隆美爾在從前線返回指揮部的途中被盟軍的轟炸機炸成重傷,被送進了醫院。
也正是在三天后,德軍東線大本營「狼穴」中發生了令人聞風喪膽的「刺殺門」事件,主人公正是病情急劇惡化的希特勒。
彼時,德國許多高級陸軍軍官對納粹黨的橫行霸道極為不滿,部隊內部更因希特勒在軍事上的冒進積怨已久。
1944年夏日,眼見德國在各個戰場上連連敗退,幾乎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卻不顧勸阻,罔顧官兵性命。
因此,德國高級陸軍將領決定就此除掉希特勒,他們制定了不算嚴密的計劃,選定了行刺人——
施陶芬貝格。
或許是他們過于輕視這個體弱之人,亦或者是對年輕的施陶芬貝格過分自信,刺殺并未成功,希特勒只是受了點輕傷。
當天,勃然大怒的希特勒便開始大規模地搜捕幕后之人,在此次行動中,約5000余人被殺,10000多人被關進了集中營,而這其中,不知情的無辜者占絕大多數。
刺殺行動當天,隆美爾正在醫院接受治療,神志不清,按理說退千百步說都沒有作案能力,且隆美爾和希特勒素來親厚,希特勒可謂是他的伯樂,誰能懷疑到隆美爾的頭上呢?
然而,誤會、栽贓……亦或是確有其事,無論如何,隆美爾的的確確被希特勒記恨上了。
希特勒在搜捕行動中獲得了一份秘密名單,「埃爾溫·隆美爾」赫然在列,且被內定為「帝國總統」。
希特勒的第一反應是懷疑:隆美爾就是一個「戰爭生物」,較之政治,他更沉迷于軍事,熱衷于鉆研戰術,這樣一個人,如果是早有預謀,他會選擇成為所謂的「帝國總統」嗎?
然而,希特勒的理智并沒有持續太久,轉念一想,如果是別人內定隆美爾成為帝國總統,那他同樣該死,因為在眾人看來,這個莽夫居然比自己更適合成為一國元首了,這對希特勒而言無疑是一種尖刻的嘲諷。
得到消息后不久,希特勒就秘密地下了決定:「干掉隆美爾。
」
與此同時,審問的結果出來了,年輕的施陶芬貝格至死都沒能流露出有用的情報,赫爾林根市市長施特羅林同樣如此,但他的助手霍法克中校卻恰恰相反。
法克德治自己注定難逃死亡的命運,與其如此,不如賭一把,說出背后指使的名字,說不定可逃死罪。
思極此處,在柏林拉菲爾旅館的一間狹小陰暗的地下室內,霍法克在黨衛軍保安局對他審訊的第二次會議中,說出了克魯格和隆美爾兩位帥的名字。
盡管黨衛軍上校對這一情報多有懷疑:「太刻意了,仿佛是一個有意為之的圈套。」
但無論怎麼審訊,霍法克依舊堅持幕后指使是這兩位帥,「我這條命留著也沒什麼用了,我現在對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感到悔恨,后悔自己當初被蒙騙,憎恨幕后的指使者。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會說假話的。」
直到格殺令頒布后,希特勒仍在思考隆美爾對自己的忠誠,他一遍又一遍地問黨衛軍帝國領袖希姆萊:「克魯格參加密謀,我想這是可能的,但是隆美爾,我想不出他背叛我的理由。」
但當希特勒聽完了希姆萊回報的霍法克供詞后,沉默片刻問道:「用了說明手段嗎?」
這依舊是對供詞的真假表示質疑。但希姆萊的下一句話卻徹底令他失去了念想:「據審訊者報告,這都是他自愿交代的,沒有用刑,此人供出所知的一切,無非是想留下一條小命。」
誰料希特勒嗤笑一聲:「這種人,絕對不能留。」
另一頭的隆美爾對即將到來的危險一無所知,他仍然躺在巴黎勒瓦西內的醫院病床上,他同妻子說,自己這次負傷應該能拿到第6條光榮負傷綬帶,并且獲得一枚傷員金質獎章。
1944年的8月7日,一切如期而至,但令隆美爾稍稍有些擔憂的是,這一次,他沒有在元首的眼中看到笑意與贊賞。
第二日,隆美爾回到故鄉,他告知妻子露西:「我這次至少得八個星期才能重新回到部隊。」
露西顯得很是開心,「我巴不得你住個八個月。」
隆美爾則很是嚴肅:「前線形勢那麼緊張,讓我在家住兩個月,這非得急死我不可。」
他親熱地撫摸兒子曼弗雷德的頭髮,「你不是已經參加高炮部隊了嗎?怎麼這時候在家?」
「我正好休假,媽媽說您回來了,我覺得應該陪陪您……」
一家人其樂融融,夾著歡聲笑語走了進去,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也是一家人最后的溫馨。
一個平靜地令人昏倦的下午,布格道夫登門拜訪,他神色嚴峻,莫名令隆美爾感到不安,原本的問候語也歇了下來,「發生什麼事了?」
「你被指控為謀害元首的共犯了。」說話間,布格道夫掏出了一封信件,「這是凱特爾元帥給你的。」隨后,布格道夫宣讀了霍法克等人的書面證詞,細細聽來,竟是證據確鑿。
隆美爾先是沉默,但越聽越氣憤,若不是元帥的尊嚴的氣度支撐著他,此刻他已經將這個無恥之徒痛罵一百遍了。
時至今日,似乎所有的辯解都已是多余,他的痛苦深藏于冷漠之中。
布格道夫宣布完畢后,似乎是在等著他反應,良久,隆美爾問道:「元首知道這件事嗎?」
直到這一刻,隆美爾的喉嚨里才發出一聲短促的哀鳴。
「看來,事已至此,我只能承擔一切后果了。」
布格道夫接著將凱特爾私下交代給他的話重復了一遍:「元首承諾,如果你選擇自盡,第三帝國會將你的叛國罪嚴加保密,德國人民不會知道,同時,保證不會對你的親屬采取任何非常手段。
」
「露西……」他心中滑過一絲掙扎。
對面卻回答道:「露西將領取陸軍元帥的撫恤金,這一切都是對你從前為帝國作出的貢獻的肯定。」
對于一個叛徒而言,看似是再好不過的「優待」,但是毫無疑問,如果隆美爾選擇申訴或者反抗,他面臨的將是身敗名裂,妻離子散,以及最為嚴厲的抨擊。
「我,埃爾溫·隆美爾經歷了無數的槍林彈雨,無數次出生入死,這一切都是為了第三帝國,但我今日卻要以叛國罪死去,死在我未曾參與的陰謀之中,為我根本不屬于的參謀總部組織而捐軀!」
他悲愴,卻無人回應,對面的人,眼中沒有悲喜,亦沒有憐憫,末了,隆美爾只是說:「元首允許一個‘叛徒’自盡,保持我的榮譽,已經是極大的厚愛了。」
「那麼,讓我們開始吧。」布格道夫有不忍,但也不敢流露出一分一毫。
隆美爾似乎又回到了那個冷酷的元帥,他靜靜問道:「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車,去往別處,安靜地離開嗎?此外,我的手還有些不便,不能很好地使用手槍。」
「我們帶來了一種特制藥,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奏效。」
「奏效」自然是指即刻死去,看來希特勒對自己這個「叛徒」確實是仁至義盡,甚至為他選擇了見血封喉的毒藥。
「謝謝您」,隆美爾沉吟道,「請給我十分鐘的時間,我得跟家人去道個別。」
布格道夫自然是隨行,雖然他看隆美爾的樣子不像是打算出逃。
汽車在隆美爾府邸外等候著,隆美爾將拐杖夾在臂下——他的傷還沒好全。
他進入屋內,看著保養良好的妻子和剛剛15歲的兒子,心中很是痛苦,他簡單地交代了幾句,從驚慌到恐懼再到不舍,露西幾乎暈厥過去,年輕的曼弗雷德則遠遠地瞄了一眼門外的車輛,不死心地問道:「就這麼赴死嗎?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然而,隆美爾只是看了一眼年幼的兒子,他多麼年輕,這是一個潛力無限的小隆美爾。
而正是那一眼,曼弗雷德便知道了,父親是自愿的。
他送別父親上車,上車前,隆美爾又把手伸出來與兒子握了握,輕聲道:「你去樓上看看你的母親。」
隨后便關上了車門,離去。
1944年10月14日,埃爾溫·隆美爾因突發惡疾在車上暴斃。
這是時人收到的消息,無數人為他痛哭,其葬禮規模堪比國葬,卻無人看到,那一日,軍帽端正的元帥闔目,那輛送靈的黑色轎車,以搶救之名穿梭人群,向著烏爾姆市醫院駛去。
鄒博主編. 世界通史 第4卷[M]. 2011
-END-
作者:理理
編輯:如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