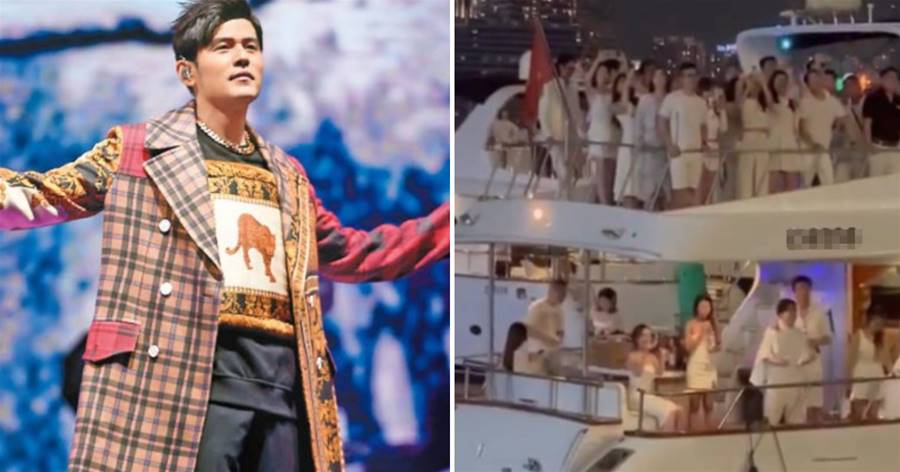文 |老涵
編輯 |老涵
周國第一次與胡國直接接觸是在公元前457年。趙的一個家族吞并了榮格,征服了泰,這樣驅逐了胡。
在史志第110章中重復,略有修改,其中報告香津「越過寇初山,吞并泰并來靠近胡莫。
對太的征服是通過奸詐的手段完成的,因為他吸引了太王和太王的官員去參加宴會,他把他們都殺了。
然后,他派軍隊去征服泰(當然,使用殺人的手段,特別是在對付周社區以外的國家時,已經成為一個幾乎不值得注意的事實)。
周陳述了與泰的關系,包括國王的領地,遵循了春秋末流行的周與非周的關系模式,也提醒我們公元前520年秦對庫里的征服。
隨著對曾經包圍周國的鄭和提民族的征服即將結束,秦國將其邊界推到他們不熟悉的胡人占領的地區。
雖然「胡」可能曾經被用作一個民族,但在前漢的資料中,它只是游牧民的通稱,在漢時代已經成為匈奴的同義詞。「莫」在前一段和「胡」一起提到,是一個古老的術語,出現在施清和周利中,指的是外國鄰居。
一般來說,沒有文本基礎表明胡或莫構成了一個或多或少同質的民族或語言群體。相反,「胡」被用作一個籠統的術語,包括從事游牧師的主要經濟活動。
因此,胡表示一種不同于榮格和提的「人類學類型」,但并不意味著不同的胡之間在語言或種族上的相似性。
根據一封寄給甄王的匿名信,陳國記載:胡人和月人不能理解彼此的語言,也不能交流他們的想法,但當他們共享的船周圍出現洶涌的海浪時,他們互相拯救,就好像他們來自一個國家一樣。
山東的盟軍現在好像是在同一條船過河,但當中國軍隊到達他們時,他們不會像他們共享一個國家一樣互相營救。
他們的智慧確實比不上胡人和岳人。顯然,這段話的意義不可能是胡和月相互接觸,互相幫助,對抗共同的威脅。
相反,「月」這個名字是對南方的非中國人的總稱,而「胡」則描述了北方的非中國人。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說,到公元前四世紀末,「胡」一詞適用于說不同語言的各種北方民族(部落、部落群體,甚至國家),通常生活在廣闊的領土上。
然而,當需要出現時,他們的分裂可能會變成一種優越的政治組織形式(一個「國家」)。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胡在出現之前經常出現一個限定詞,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特定民族的標志,比如林胡和東胡。
不管它最初是不是一個民族,這樣的名稱在戰國晚期已經消失了。
根據拉蒂摩的說法,中國資料中出現的北方民族的「新名稱」反映了非中國民族經濟專業化的變化,因為他們被強行驅逐到一個更加干旱的生態區。
拉提摩認為,胡和匈奴是古代的榮格和提,一旦被擴張中國政治而推入大草原,他們就轉向了游牧的生活方式。
然而,根據之前提出的考古證據,這一有影響力的論點不能成立,這些證據表明,從半宗教農業畜牧業向游牧主義的轉變發生了很長一段時間。
筆者認為:事實上,在著名的「胡」服裝糾紛之前,我們對北方中國人和游牧民之間的關系知之甚少也就是說,一種適合騎馬的服裝——導致曹國州采用了騎兵,這一重大事件標志著北部邊境對北部各州的國家建設進程日益重要。
沒有提及入侵、提交、戰爭和法庭訪問,但我們確實發現了關于貿易的零星暗示,表明游牧民族和定居的民族享有和平的關系,雖然遙遠,而且似乎與他們之間存在一種地方性的、不可調和的敵意相矛盾。
與七世紀和六世紀的提和榮格相比公元前,北方游牧民族從450人到330人公元前是一個馴服的鄰居,遠離他們後來變成的危險的地段。
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間關系似乎繁榮的一個領域是貿易,這一考慮不僅得到考古數據的支持,而且得到文本參考文獻的支持。在陳國中,有邊緣但明確的跡象表明,胡國與胡相互貿易,胡向周國出口馬和毛皮。
另一個例子是《木琴宗傳》(木琴宗父子傳記,通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三世紀左右),雖然大部分是虛構的,但它提到的信息一定起源于實際的實踐和習俗。
在他傳奇般的旅行過程中,穆皇帝與他遇到的外國首領交換禮物,這可能是公元前四世紀中國和北方牧民關系中的一種常見做法。他收到的最大的「禮物」是牛羊的形式,有數千只,這表明存在著專門的田園民族(不管他是否真的拜訪過他們)。
作為禮物,更有價值的是馬,它總是排在任何名單的首位,有幾百匹。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很重視馬,馬在中國長期被用于軍事和儀式目的,但北方有多余的馬出售給中國。
第三種禮物是谷物,但并不總是出現,比如小米,這表明至少有一些北方人依賴于農業和畜牧業;其他的「捐贈」包括葡萄酒、狗和山羊。
皇帝穆提供的禮物作為回報主要是珍貴的文物,如鹿由銀或金,銀鳥,黃金項鏈或寶石珠子,珍珠,金條,腰帶裝飾著珍貴的貝殼,有時,好的馬在一個團隊(四個相同的顏色),可能是為了把皇家馬車和用于顯示。
婦女的禮物被用來鞏固一個聯盟,這一做法表明了新娘送禮是一種外交手段的作用。這些禮物能在戰國晚期游牧墓葬中常見的青銅鹿和金色的動物風格牌匾中找到它們的材料嗎?
目前,我們只能登記考古發現和木皇帝旅行的可能融合,注意到考古學似乎證實了木宗川中提到的貿易。
其他零星的參考資料也使我們能夠辨別出外交和經濟交流的趨勢,即田園產品被交換成諸如絲綢等高價值的物品。
在《志志》第129章中,我們發現「肺人和志志以北的土地上有豐富的馬、牛、羊、毛氈、毛皮、肌腱和角。」這片土地的商業價值并沒有被商人吳志失去,他在秦第一皇帝時期變得富有。
他用絲綢換成了家畜隨著榮格部落的國王,從而極大地增加了他自己的馬和牛群的規模,他們的數量「只能由山谷來估計」。
「我們不知道這位國王是誰,但這個故事證實了公元前三世紀大量貿易的存在。當時,中國國家也從泰進口馬,這個地區被稱為鈦領土,其居民有城市中心,并被組織成「國家」。
馬的出口的榮格和Ti民族,來源參考,可以反映國內生產的牧民或農業牧民或指出間接貿易的現象,這些部落采購馬間接從游牧民族的北方和西方和賣給中國。
最后,除了其他來自中國的物品,如刻有重量的金牌匾,在北部地區還發現了大量的硬幣。
筆者認為:硬幣和黃金無疑表明了一個復雜的商品循環網絡,盡管其機制還不太清楚。然而,要假設貴金屬制品和可能的絲綢被交換馬和毛皮,而這種易貨貿易是貨幣貿易的補充,并不需要多大的想象。
但是,貿易問題不僅必須考慮交換,而且必須考慮進入市場和通訊路線。例如,蘇馬琴似乎暗示了公元前四世紀。
擴張欽因進入榮格和提的土地,不僅是為了促進與外國人的貿易,而且也是為了與欽的繼承國開辟直接和安全的路線。
這種擴張阻止了邊緣民族,如鄭人和泰人,在北方州之間以及北方州和游牧民族之間的商業交流中扮演中間人的角色。
筆者認為:後來關于鹽和鐵的論述(楊特倫),可能發生在公元前86年到81年之間,也指繁榮的北方貿易,包括從中國和胡進口毛皮和動物(不僅是馬,還有其他家畜,如驢和駱駝),以換取一些黃金小飾品和一些廉價的絲綢。
在公元前一世紀,這一論點被用來為漢武帝的擴張主義計劃辯護,但沒有理由認為這種貿易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
如果我們假設中國與北方的貿易是基于中國對馬匹的需求,我們就必須問一下,為什麼到底需要這些馬匹。
最明顯的答案是,當中國國家開始創建騎兵部隊時,馬匹成為了一種需求。采用騎兵產生了經濟和軍事上的后果,因此,這被普遍認為深刻地改變了北方和中國之間的關系。
關于在中國采用騎兵的核心文本證據是在307年舉行的一場著名的辯論公元前,在趙國王的宮廷里辯論是關于采用騎兵和騎兵的,受游牧民族的啟發,得到了一位有遠見的國王的堅定支持,反對他的顧問們的保守態度。
這場辯論展示了趙國蘭和鄰國之間關系的全貌。此外,它還表明,促進這一軍事改革是為了加強國家對抗所有敵人,而不是作為擊退突襲的游牧民族的特別措施。
國王的主要目標是把他自己的中國人民變成騎兵的戰士,部署在曹國蘭與中國和游牧國家的邊境上。
但值得懷疑的是,他的新軍事機器實際上被用來「遏制」各種胡,因為在這個時候,對趙作為獨立王國存在的最大威脅來自其他中部國家;事實上,在幾十年內,趙被秦入侵和征服。
武陵王在辯論中的立場絕不是完全的,甚至主要是防御性的。
事實上,他的言辭完全集中在進攻性軍隊的發展上。趙外交政策的兩個目標,即完成吳陵王的前任發起的領土征服和建立對中山的防御,第一個是公開擴張主義的。
征服林和國郎的城市是在大約30年前,當趙打敗了林虎游牧民,28歲,國王相信鞏固這些領土收益和進一步擴大國家擴張的時候已經到了。
憑借馬基雅維利式的決心,國王決定推動這一變革,盡管人們可能會嘲笑他,不是因為他希望鞏固自己,反對襲擊的游牧民族,而是因為征服胡族的土地和中山國是他的政治計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的歷史地圖集》
《馬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
《亞洲的土地和人民》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
《中國古代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