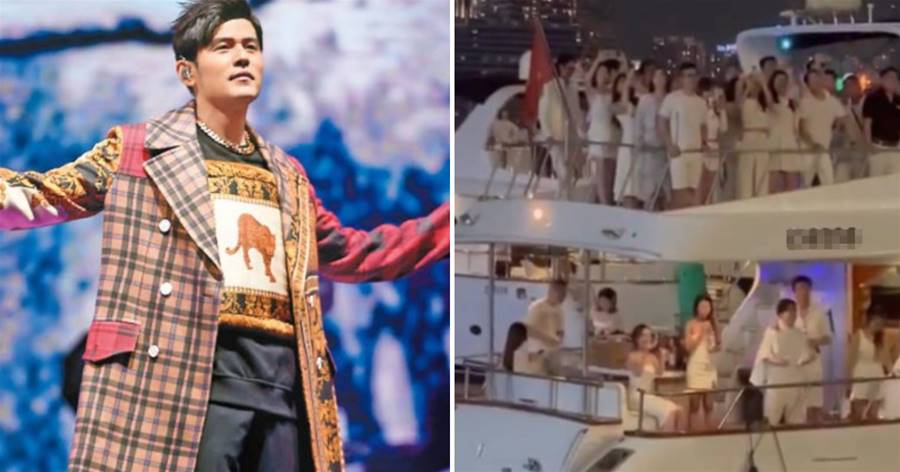文 |老涵
編輯 |老涵
在周國之間致命斗爭的背景下,非周國往往是一種重要的軍事資源。在公元前649年。許王的兒子泰召集的幾群人聯合起來攻擊都城。
他們的陰謀失敗了;泰受到懲罰,在蔡尋求庇護。蕭王和榮格的關系變得緊張,我不得不擔任兩黨之間的調解人。
在另一個例子中,公元前627年,秦動員了蔣榮,在他們的幫助下打敗了秦。然而,三年后,秦再次進攻秦,收復了失去的領土,成為西方榮格的君主,后者承認自己的霸權。
秦最初是如何使用蔣榮格的?他們之間關系的確切性質是後來才出現的(公元前559年)。在蔣鐘和秦大臣范賢祖的爭吵中。
為了防止蔣榮的頭參加一個大型的州際會議,秦高官聲稱榮格首領的一位祖先,只穿著稻草,來尋求秦的保護,他和他的人民得到土地耕種。
榮格現在沒有表示感激,而是散布關于秦的謠言,在其他周國家中損害了國家的聲譽。
因此,榮格酋長將不被允許參加會議。榮格貴族(一個「子爵」,或tzu)的答復明確表明,秦一直在利用榮格作為加強國家的資源。
他說,當時秦因正在迫害他們,秦的許公爵,他認為榮格是「四山」的后裔,他們就容他們定居在南部邊境,一個被狼和狐貍困擾的荒涼的土地。
榮格84年清除了這片土地,表現為忠誠的臣民,甚至給予欽軍事支持反對欽:「如果軍隊沒有回到它的國家也就是說。
它被消滅了——榮格的首領說——這要感謝我們。」他指出,鐘格在軍事和政治上是對秦的寶貴援助,如果「你們的軍官軍隊犯的一些錯誤造成了與其他周領主的距離」,現在就沒有責任了。
在撤退之前,榮格酋長說:
「我們榮格的食物、飲料和衣服都不同于中國(華),我們不和他們交換絲綢,我們的語言也不能相互理解。」
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來表示華夏和榮提之間的文化距離。
表明,這種文化距離并不意味著政治距離:榮格是周政治的組成部分,是額外的一部分士兵和農民的來源。
公元前533年,秦被指控有罪。依靠外國軍隊打擊的核心周政治體系表明,這個時候外國軍隊可能被用在如此大的數量,他們構成一個單獨的力量在中央國家,他們的存在只是成為焦慮的來源。
中國較大的國家吞并和使用非周民族,平行于新行政區劃的劃劃和軍隊規模的增長。
再次以秦為例,在632年公元前629年,為了對抗鈦。在現有的三支軍隊中增加了三個縱隊公元前,軍隊增加到5支,也在588年作戰。
在鄭和帝人被迫合并后,秦的軍隊增加到6支——只有周家可以指揮一支90人的軍隊——很可能有很多新軍隊新兵來自被征服的榮格和提人。
一些鈦在受到其他人的威脅時也自發地向周國投降,并可能提供他們服兵役以換取保護。一些提部落也非常容易被征服,比如當魯國打敗了可能屬于提」星系的肯謀人時。
筆者認為: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明確地表明,到公元前6世紀末,鈦族人民已經完全融入了中國各國的軍事機構。
非周族加入了周族的軍隊,以及與他們的曠日持久的戰斗,也促成了周族軍事戰術的重大變化。
到公元前541年。秦的狀態已經向其戰車軍隊轉變為一個步兵,這將更能適應崎嶇的地形,并專門打算與榮格和Ti步兵作戰。
部隊中對這一過渡的抵抗一定是相當大的,因為對拒絕服從的士兵所施加的懲罰是死亡。
隨著勝利的周國不斷合并外國人民,他們政治的擴張需要新的政府體系在政治和行政上吸收他們;因此在公元前七世紀。
周族制度是作為一個新的行政單位而創建的,旨在納入新的主體,其中許多人實際上是非周族。如何保持他們的忠誠的問題也被討論過了。
揭示在公元前538年中國高官的譴責他的主,他告誡主,傲慢或不虔誠的行為會導致彝族,榮格,提反抗,統治者的能力管理外國人民的公平手段而不是強迫的是他的精湛的一個基本屬性。
春秋時期見證了周族與非周族之間新關系的興起。在商朝和西方的商朝(一邊是商朝和後來的周朝)之間經常發生戰爭,另一邊是位于兩朝核心區周圍的許多民族。
然而,管理他們關系的原則是不清楚的,我們留下了一個邊境的形象,那里的軍隊是最高的,來自中國國家的外國遠征,以及外國人的敵意入侵。
然而,從周東方開始,周國和非周族(其政治組織水平難以評估)之間的政治關系變得更加規則和正式。
這種關系在三個層面上發展:被周國對非周政治的征服,周國與非周國之間的外交交流,以及將非周國納入周國擴張的領域。
只要有可能,周國試圖征服北方非周民族并合并他們。這一政策尤其在公元前八、七和六世紀得到實施。
由最積極的擴張主義政治政體,即秦、秦和秦。通過外交手段--會議、條約、人質交換和訪問告上法庭——周列國試圖盡可能長時間地維護與外國勢力的和平。
國家在和平時期的目標包括節約資源(人員、武器、設備和食物),展示睦鄰友好關系,以及雇傭外國人來捍衛國家利益。
當他們征服外國人時,各州利用它們來增加軍隊的規模,保衛邊境,并開辟新的土地。
這樣,榮格和Ti就成為了國家爭奪霸權的基本因素。與此同時,還制定了各種關于周氏國外交關系的學說。
在一般層面上,特別是在協議和程序方面,這些學說被大多數參與的政治體所遵守,無論是在周的政治和文化社區內外。
然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些學說應用于非周民族的方式存在顯著差異。
在這方面,我認為,盡管人們用假定的道德差異來解釋敵人為「可征服的」,但這些道德主張既不是固定的,也不適用于每一個外國政體。
對它們的背景的仔細分析表明,它們是政治發展的產物而不是在周政治文化社區中正在發展的文化凝聚力的跡象。
對那些在原則上至少沒有被視為外國的國家實施同樣的道德制裁,清楚地表明,「道德」或「文化」共同體的概念仍然是流動的。
這種流動性反映了周東方的政治背景:在外交關系中,道德話語完全服從于戰爭和激烈的軍事和政治競爭,并適應了當時的緊急情況。
看周國家與外國人民的關系從這個角度,是否「軍國主義」或「和平主義」學說出現反映了特定狀態的目標在一個給定的時刻而不是更大的周(中國)文化意識表達自己的「道德內部人士」和「不道德的局外人。」
佐川和郭宇的歷史信息也表明,道德考慮是次要的,僅次于我們所謂的鎖定致命戰斗中的政治的「理性選擇」。就在公元前五世紀末。提和榮格似乎作為獨立的政治體基本上被淘汰了。
那些幸存下來的人,比如中山州,只在名義上是外國的,而事實上,它的居民在文化上與周州的居民沒有區別。
政治吸收和文化同化的過程使中國北方國家接觸到另一種類型的人種學和政治現實:北方游牧民族。
榮格人和提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牧羊人或登山者,他們的軍事技能很容易與之媲美,而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戰術和技術,尤其是與騎馬有關的,構成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接下來的前帝國時期的北部邊境歷史講述了這次相遇及其對中國和亞洲內部的歷史的后果。
在前帝國主義的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時期像戰國時期(公元前480-221年)那樣改變了北方邊境的物質方面和政治意義。
在中國,國家權力的增長和軍隊規模的增加需要國家資源的不斷擴張,迫使每個統治者都要找到最大化自己資源的方法,并試圖壓制對手的優勢。
在戰國后期,領土擴張的趨勢持續穩定,北部的秦、延安和趙小蘭三個州試圖擴大他們對新土地和民族的控制。
筆者認為:北部邊境是國家擴張進程的一部分,但與前幾個世紀相比,中部各州現在面臨著一種新的、要困難得多的情況。如第三章所述,中國北方田園文化的發展,形成了貴族游牧民族的軍事社會。
作為一種新的「人類學」類型,游牧民族以胡的名字出現在漢語中。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的:他們飼養動物,騎馬戰斗,擅長射箭。
胡可能被組織成分為血統和部落的等級社會,很快就證明有能力創造類似帝國的政治單位。
他們剛到中國北方嗎?在公元前五世紀和四世紀,當然不是,但我們的知識僅僅是基于考古材料,而且仍然沒有絕對的年表。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田園生活游牧文化可能在公元前7-6世紀就已經成熟了,盡管它們當時可能被限制在較少的中心,并與半定居的民族混合在一起。
從他們後來的成功來看,這些軍事團體在軍事上可能比毗鄰中國的農牧社區組織得更好。
榮格逐漸消失的歷史記錄——盡管他們的名字繼續使用修辭或痕跡——很可能不僅這些集團的同化的中國國家也游牧群體的力量增加他們的統治對這些民族,將他們在自己的政治。
戰國后期發生了兩件重大事件:采用騎兵和在北方建造了被稱為「長墻」(清長城)的軍事設施。
所謂長城的前身,長長城構成了軍事防御工事的北方線,後來在他統一中國后,由其連接成一個單一的體系。這兩項事態發展都促成了北方明顯的軍事化和「更硬」邊界的形成。
《野蠻人通過中國人的眼睛:研究種族差異的人類學方法的出現》
《中國古代考古學》
《中國文明的起源》
《華盛頓:人類研究所》
《代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中國文明起源的過程方面》